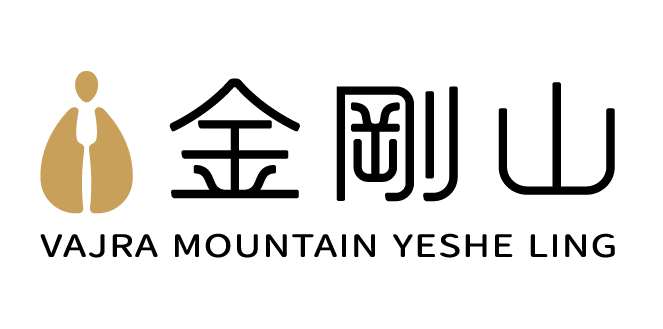太虛大師 著序
修印法師 開示
今天講的課,對我們弘揚《廣論》非常重要,為什麼呢?當然是事出有因。在早期藏傳佛教--跟我們台灣的佛教界,沒有那麼頻繁互動的時候,有些人他扛著是修密的,但是在修為上就是很不如法;本來這是他個人的問題,可是最近幾天有人一直問我:他對佛教,尤其是對密教,總覺得好像是一種邪教?我就跟他們說:「道在人弘,佛法是教導我們修行的。如果佛法被一些不法之徒拿去貪圖他的名利,當然我們也沒有辦法!」我就舉個很實際的例子給他們聽,我說:「像現在,專賣僧服的,專賣佛教文物的,都有賣出家人的服裝,那麼你要藏傳的服裝也買得到,要漢傳的服裝也買得到,即使買不到,你也可以請人家特別為你訂做;所以只要一個人,他心存不軌,他想要扮演佛教的出家人,無論是扮演漢傳的、藏傳的,我們都拿他沒辦法!」那麼我們可以做的是什麼?我們弘法的人,認真的把這麼好的教法弘揚出去,去廣利眾生,眾生真正學到了法要,就有智慧去分別──我們能做的只有這樣。對方聽了,就頻頻的點頭。
那天,我又跟一些老信徒座談,他們也是提起這個問題,他們說:「我們的觀念裡面,覺得《廣論》是一位密宗的人所寫的。而密宗本身就有一種非常神秘的色彩。」在他們的想法裡:既然覺得是很神密的色彩,難免就興起到底接觸好?還是不接觸好?如果接觸了,真的是接觸到了邪教、邪思,那麼就不要接觸好;可是聽人家又說《廣論》是這麼好,內心裡面又覺得沒有學習也真的很可惜!所以,我當時引用了太虛大師的序文,說給他們聽。可是我想想:每有這樣的音聲我就說一次,每有這樣的音聲我就說一次,那又何其多!還好他們有發出音聲,也剛好我有跟他們座談,不然那些没有發出音聲,而我没有跟他們座談的,要如何淨除心中的疑惑呢?所以我就想:乾脆就藉著這樣的因緣,把太虛大師的序文說給大家聽。因為我們在推廣《廣論》,在弘揚《廣論》,所以我把宗大師所說的幾個很重要的地方,說給大家聽;那麼,以後只要人家一問起,你們內心裡面就知道怎麼去回答他。
法,是因為人而弘的,對不對?道,也一樣,因人而弘。在中國佛教有一句話說--如果正的法被邪人拿去弘揚,正法就變成邪法;大乘的法被小乘的人拿去弘揚,大乘的法也變成小乘的法;反之,大乘的人弘揚小乘的法,小乘法也會變成大乘法,變成大乘之用,所以「人」是非常重要的。那麼,如果我們的心,我們的等流--尤其是我們的心今生沒有想要,那麼學了再多的法,我們的自私之門還是把自己罩住,因為我們的心本身有某一種東西障敝住,再好的法要,對我們來講,都是沒有辦法可以達到那一種精神,這一點大家一定要記住。
我們看《廣論》第一頁--序,作者是太虛大師。從《廣論》這一篇序文,還有略論的序文,我們知道太虛大師是清末民初的人。在那個時候--清末民初,中國正面臨戰爭,國內唯有的就是戰爭,毀壞佛教。太虛大師生在這種苦難的時代,非常有心要去振興佛教;雖然時局就是如此,但是他還是不被時局所影響,盡自己最大的力量,要去振興佛教,所以,我們現代的佛教界才會讚嘆太虛大師,說他是佛教的改革者。為什麼是改革呢?我認為與其說改革,不如說振興,因為佛教本來就是那麼好,其實是不須要作什麼改革,而是人把它造成弊病,所以現在我們把這些弊病消除掉,讓原有的佛教--那麼的莊嚴、那麼的神聖、那麼的清淨--展現出來,這就是我自己的認為。太虛大師生長的那個時代,真的是一個苦難的時代,所以現在對我來講,每一分每一秒可以研讀佛經,都是非常珍貴的。這也是我一直以來的思惟。
現在我們就來看這一篇序文。
這篇序文對這本《廣論》的宣揚,有很大的幫助。
大家翻開《廣論》第一頁序文,就是太虛大師為這本《廣論》所作的序。
【比因西藏學者法尊譯出黃衣士宗喀巴祖師所造菩提道次第廣論,教授世苑漢藏院學僧,將梓行而問世。】
這一段太虛大師這麼說:近來因為西藏學者法尊法師,翻譯出黃衣士宗喀巴祖師所造的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,他翻譯這個要作什麼呢?要教授世苑漢藏院學僧。「將梓行而問世」,即將出版流通。
【余為參訂其譯文,閱至「如是以諸共道浄相續已,決定應須趣入密咒,以能速滿二資糧故。設踰共道非所堪能,或由種性功能虛劣,不樂趣密咒者,則唯應將此之次第加以推廣。」】
「余為參訂其譯文」,說我為這本翻譯的《廣論》,參加審訂、校稿它的譯文。
「閱至」,說我看到。「如是以諸共道淨相續已,決定應須趣入密咒,以能速滿二資糧故。設踰共道非所堪能,或由種性功能虛劣,不樂趣密咒者,則唯應將此之次第加以推廣」,太虛大師看到這一段文,他有一個感想,所以說「閱至」。他看到的是哪一段文呢?在《廣論》的七十一頁,說「如是以諸共道淨相續已」,這是宗喀巴大師因為前面講述,講到這個地方,他就這麼說:像這樣用「諸共道淨相續已」,「共道」,就是大家所共同之道,所共修之法;也就是顯教。「淨相續已」,清淨的相續,清淨了我們的內心以後。「決定應須趣入密咒」,因為我們是要成佛,成佛要福智二資糧圓滿,所以說「決定應須趣入密咒」,一定應該要趣入密咒。為什麼要趣入密咒呢?「以能速滿二資糧故」。因為你趣入密咒以後,就能夠快速的圓滿福智二資糧,所以宗大師鼓勵人家,一定要趣入密咒。
「設踰共道非所堪能」,假設趣入密咒,那當然就是超越了共道,所以說「設踰共道」;假設超越了共通的法要,共通之道,「非所堪能」,就是不是自己的因緣條件所能的。不是自己的因緣條件所能的話,「或由種性功能虛劣」,這個「或由種性功能虛劣」,可由幾點來說:第一點、也許他的年歲已經非常老了,才學佛,那麼在一些法要上,有時候他是沒有辦法去修的;再來就是他根本沒有菩提心,没有菩提心,也是屬於「種性功能虛劣」,也就是說他沒有大乘種性,他只求自我的了脫。「不樂趣密咒者」,或者他根本沒有興趣修這個密法。
「則唯應將此之次第加以推廣」,這個「唯」字,就是希望。那麼希望應將這個次第來加以推廣。我們看宗大師並沒有說,你們不這樣一定是不行;他說:如果你覺得或由種性功能虛劣,或由不樂趣密咒者,那麼希望你應該將道次第加以推廣。
當然《廣論》是一本一直在闡述道次第法要的經典,所以我們可以以《廣論》來講說,將這個道次第加以推廣。「加以推廣」是什麼?推廣,其實可以用另外一種說法,也就是依照《廣論》所教的道次第,去深修廣行。從菩薩道來講,當然就廣行菩薩道,你一遍一遍的串習,串習到後面,還有奢摩他、毗缽舍那,這些都是深修──既深修又廣行。所以把自己所修的,所證的去弘揚開來,也就是推廣的意思。
【其為特尚密宗之理論,甚為顯然。】
「其為特尚密宗之理論,甚為顯然」,這一句是太虛大師所講的。他說:「由這一段文我們就可以看到,宗喀巴大師特別的崇尚密宗的理論是非常的明顯。」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,宗大師確實決定應須趣入密咒,所以太虛大師才會在這裡,下一個這樣的言語--「其為特尚密宗之理論,甚為顯然」。
可是太虛大師的心胸廣大,他下面就說:
【例之賢首以別教一乘特尚華嚴,天台以純圓獨妙特尚法華,固將無別。】
「例之賢首以別教一乘特尚華嚴」,「例之」,就是例如。「賢首」,就是中國的賢首大師。「以別教一乘特尚華嚴」,是說賢首大師認為華嚴經是佛特別為大乘菩薩所宣說、所教導的最究竟一乘佛法,所以,賢首大師特別崇尚《華嚴經》。我們中國的八宗,都有他自己所依據的經論,譬如說賢首宗,也叫做華嚴宗,當然賢首大師就特尚華嚴;因為他將華嚴經認為是佛特別為大乘菩薩所宣說、所教導的,是最究竟的一乘佛法,最圓滿的佛法。所以這裡說「以別教一乘特尚華嚴」。
「天台以純圓獨妙特尚法華」,天台宗因為智者大師在天台山修行,所以後來就把智者大師所崇尚的法華經稱為是天台宗,也叫做法華宗。「天台以純圓獨妙特尚法華」,是說天台智者大師以法華經為根據,認為法華經是佛法當中最純的,就像是最純的牛奶,直接從牛的身上擠出來,没有滲雜一點點的水,或者是其他香料等等,所以是最純的、最圓滿的、是獨一無二的、是最殊勝微妙的,所以說「天台以純圓獨妙特尚法華」──他特別的崇尚法華經。
「固將無別」,這個「固」,就是本來,本來就沒有差別,本來就一樣的。宗大師特尚密宗,跟賢首大師特尚《華嚴經》,智者大師特尚《法華經》,本來就是一樣的,無二無別的。
【然中國尚禪宗者,斥除一切經律論義,雖若宗鏡錄遍錄經論,亦但揚厥宗,鄙餘法為中下。】
「然中國尚禪宗者,斥除一切經律論義」,可是不同的是什麼?同樣都有所崇尚,可是不同的是中國崇尚禪宗的人,「斥除一切經律論義」,呵斥、排除一切經、律、論所說的道理。這個「義」字,是指經、律、論所說的這一些道理。
「雖若宗鏡錄遍錄經論,亦但揚厥宗,鄙餘法為中下」,說即使像《宗鏡錄》遍錄經論,廣泛的收集三藏十二部經典裡面這些經論的道理,可是「亦但揚厥宗」,也只是宣揚他自己的宗義,他自己那一宗的理論,所以叫做「但揚……」,也只是宣揚自己那一宗的理論。而「鄙餘法為中下」,不只是宣揚自己那一宗的理論,而且又鄙視己宗之外的其他法門,其餘的佛法。怎麼的鄙視呢?就是鄙視其他的教法是中等的、是下等的,而自己的宗--禪宗是上等的,所以說「鄙餘法為中下」。再來說
【尚浄土者,亦勸人不參禪學教,專守一句彌陀。】
「尚淨土者,亦勸人不參禪學教,專守一句彌陀」,崇尚淨土的人,也勸人不要參禪、不要學教,而只要專守一句彌陀名號就好。你看,這是我們中國的祖師所寫出來的,都是一種深深的感慨之言。也許你們一出家,就在般若學院,就一直學著《廣論》這麼有次第的教法,所以你們感受不深!像我出家的時候,真的就像大師所講的,所以我的感受就很深很深!因為從年輕一直到現在,我看到禪宗「斥除一切經律論義」,其實就是斥除禪宗之外的修法;我看到淨土宗教人不要參禪、不要學教,「專守一句彌陀」,你看這些講經說法者、在上領導者、具有影響力的人,他們言語當中,一直不斷不斷這樣的宣說,你們想一想,在那個時代,如果你不參禪,你不唸佛修淨土,那麼你幾乎就被人家視為你是沒有在修行的。所以我常常很感慨的這麼說,我說:「難道釋迦牟尼佛沒有智慧去看到--只有一句阿彌陀佛就好,只有一心打坐就好?為什麼釋迦牟尼佛在二千多年前,他身體還好好的,不這樣的宣說,而去講浩瀚無涯的經、律、論三藏呢?一直到了二千五百多年後,才被後人把他推翻,為什麼?這到底是釋迦牟尼佛的錯呢?還是後人的錯呢?」我一讀再讀,內心裡面真的會非常的痛!我們再看
【賢台雖可以小始終頓藏通別圓位攝所於佛言】
「賢台雖可以小始終頓」,這裡可以再加一個「圓」字--「賢台雖可以小始終頓圓」。太虛大師為了使整個文句順暢,所以他省掉一個「圓」字。
「賢台雖可以小始終頓圓,藏通別圓」,這個「小始終頓圓」,是賢首宗所判,「判」就是分判的判;「藏通別圓」,是天台宗所判。這句話,我簡單來講,大家就可以知道。在歷史的記載當中:釋迦牟尼佛夜睹明星成正覺,一開悟以後,他就一直大聲的喧唱說:「奇哉!奇哉!一切眾生皆有佛性,但是只因妄想執著而不能見得。」簡單來講,釋迦牟尼佛一開悟以後,啊!一切眾生皆可成佛,可是為什麼他們沒有成佛呢?因為眾生被自己的妄想執著所蓋覆,所以讓他的佛性沒有辦法可以顯現,所以就没有證到佛果位。
釋迦牟尼佛一開悟以後,他就開始宣說高高大法──《華嚴經》,可是當時實在沒有幾個人聽懂,只有那些高高的大菩薩們才聽得懂,於是釋迦牟尼佛進入思惟了。這好有一個比喻,我說給大家聽:我們有一位同修,他在數學上非常的厲害,從學校畢業以後,還沒找到工作,這時有一位夜校的老師要生産,因此人家就介紹他去代課。他代上的數學課,學生都聽不懂!因為他是代課老師兼班導師,當然要批改週記,所以他就看到週記裡,有學生這麼反映說:「老師,你的人實在太好了,可是你的數學要再跟我們老師學習。」一看到那篇週記以後,這位同修就說:「這就是有經驗跟没有經驗的差別!」我們想一想,高中生夜校的數學能教什麼程度呢?老師,最初一定是把自己本有的都教出來,可是學生反應遲鈍,所以老師只好退而降其次,退而降其次,降到最後,就是拿出學生所要的,這樣大家快樂,學生也很滿意,老師也輕鬆。而我們這位同修,他是剛從學校畢業,所以就把他學校所學的一五一十地教,結果學生的反映,就是要他再跟他們的班導老師學習,他覺得很好笑,他說:「哦!我現在才知道,給眾生不必給的太多,給眾生他需要的,這就是最高明的老師了。」那麼釋迦牟尼佛也是啊!他一開悟以後,開始把佛陀的本地風光都講,講得大家聽不懂,只有那些高量菩薩才聽得懂,所以,釋迦牟尼佛就静下來思惟,思惟眾生需要的是什麼?
釋迦牟尼佛經過一番思惟以後,就走到鹿野苑為這五比丘宣說四諦法。最初他講《華嚴經》,叫做華嚴時。然後在鹿野苑所講的,叫做阿含時;因為他在這裡,用十二年在講《阿含經》,《阿含經》針對的是什麼?要怎麼的去斷煩惱,尤其我們這個五蘊身,是苦空的、無常的,要怎麼去斷煩惱──這階段叫阿含時。慢慢慢慢,他覺得眾生的根基已經漸漸的成熟,他就再講一些大乘法,這個時候叫做方等時──「方」,就是廣大,「等」,就是平等,再講一些廣大平等的法要,所以叫做方等時。慢慢慢慢,眾生又成熟了,可以再講一些甚深的般若法要,所以這個階段稱為般若時。那麼已然經過幾時啦?華嚴時、阿含時、方等時、般若時。般若時講的很長,像《大般若經》都是在般若時所講的,在般若時總共就講了二十二年。一直到佛陀看到眾生的因緣成熟了,可以把真正佛法的真面貎講出來,這個時候他講《法華經》,所以《法華經》佛陀用了八年去講──在他最後八年講的。而《法華經》整個的要義是什麼呢?就是匯三乘為一乘。佛陀在講《法華經》當中,就告訴弟子說:「我以前所講的,就是為了接引眾生的根基,所以我權開三乘。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成佛,我真正來到這個世間,就是要度你們成佛。」所以叫做匯三乘而歸一乘。在《法華經》講完之後,佛陀將要入滅的時候,(佛陀是十二月十五號入滅),他用很短的時間一日一夜,宣說《大涅槃經》。《大涅槃經》開示:一切眾生皆可成佛,人人皆有佛性,佛陀就一直在闡述這個道理;講完以後,佛陀就入滅了;所以這個時期是歸為法華涅槃時,把法華經跟涅槃經併在一起,叫做法華涅槃時。為什麼?因為涅槃經的時間非常的短,所以佛陀把它歸入在這個《法華經》當中,叫做法華涅槃時──這是佛陀的一代宣說佛法。把它分成五時:華嚴時、阿含時、方等時、般若時、法華涅槃時,這是天台宗的分法;天台宗依照佛陀開始講經到佛陀入滅,判為五時。
華嚴宗的判法,不是依時間的而判,是用深淺次第分判,因為華嚴宗認為佛陀的講經說法,最初就是講《阿含經》,所以判為小乘教;再來慢慢就講到《解釋密經》,然後就是《般若經》,這就是大乘的開始,所以大乘開始於《解深密經》與《般若經》,華嚴宗因此把它畫分為「始教」,「始」就是開始的始。再來佛陀就講《楞伽經》,華嚴宗認為《楞伽經》是大乘教的一個終究的教法,所以就把這個階段判為終,叫做「終教」,「終」就是臨終的終,是究竟的教法。此外,華嚴宗又認為佛陀的教法有時候是不一定的──它是一種特殊法,這種特殊法是針對一些根性特別銳利的眾生講的,叫做「頓法」,何謂「頓法」?像我們從一樓到十樓,常理來講是不是走樓梯,一樓、二樓、三樓,……一直走上去,對不對?這個是常理;可是有的眾生是頓根的,「頓」不是遲鈍的鈍,是一種很銳利,很銳利的根器,那麼這時就不一定要按理出牌了,而是用頓的,就讓他直接跳到非常高超的境界,這個就是頓──「頓教」。在頓教當中,當然又有非常圓滿的教法,這個教法就是在華嚴經與法華經中所開示的圓融不可思議的法門──匯三乘歸一乘的圓滿法門,所以又叫做「圓教」。這是華嚴宗的判法,因為它是以佛陀針對眾生根基的淺、深、頓、劣講經說法,所以把它排成五門--小乘教、始教、終教、頓教、圓教,所以叫做「小始終頓圓」。
剛才我先講天台宗對佛陀的一代時教,判為五時──華嚴時、阿含時、方等時、般若時、法華湼槃時,對不對?而對佛陀教化眾生的教法來說,天台宗把它分成「藏通別圓」。最初期佛陀所講的經、律、論,是對小乘根基所講的,所以把這個時候判為是「三藏教」,這是天台宗所判的。那麼「通」呢?通,就是眾生慢慢慢慢根基成熟了,佛陀也講一些大乘法門;也就是從小乘教--主要是講小乘教法,也開始偶爾偶爾宣說大乘教,所以這個時候,也通於大乘教教法,因此,第二階段天台宗就判為是「通教」。「通教」就是三乘所通學的教法,而三藏教是正對聲聞、緣覺的教法;通教就是三乘通學的,但是已經以菩薩為主要對象,二乘為次要的對象,也就是主角是菩薩,配角是二乘。再來,跟《華嚴經》一樣,他們又有一個別教,別教是什麼?就是佛陀講這個高高大法、無量大法,是特別對菩薩根基所講的,所以是「別教」。「別教」就不通於二乘了,所以用一個「別」字,是特別的。再來就是「圓教」;「圓教」,我們從文字就可以知道,是最上、最利的菩薩,他們已經都是事理圓融,對佛法都是事理圓融的中道實相,已經能夠契入到事理圓融的中道實相者,當然就是最上等最上等根的菩薩才聽得懂。這是法華經裡面所列的四教--「藏、通、別、圓」四教。這四教就是為化導眾生,利益眾生的法門,所以又叫做「化法四教」,「化」就是教化,「法」就是佛法,教化眾生的法門就是這「四教」──化法四教。
天台宗除了「化法四教」,又有一個「化儀四教」,「化」是教化的化,「儀」是儀式的儀、儀軌的儀──化儀四教。「化儀四教」是什麼?其實我從它整個的內容去看,「化儀四教」應該是教化眾生的方式、方法。「化法四教」是教導眾生的這些法門,這個內涵;「化儀四教」是什麼呢?第一個也是「頓」,就是為上根的說這種特別教、圓滿大教;特別法,圓滿大法,所以列為「頓教」,這是化儀四教之首。第一個就是頓教,第二就是「漸教」;「漸教」,就是對中下根器的漸次的開示,由淺入深有次第的教導。第三個叫做「秘密教」;密秘教就是佛陀用不可思議的智慧神通之力,使聽眾能各自領會,而互不相知;因為他們是各自領會,互不相知,所以叫做「秘密教」。再來就是「不定教」;不定教是什麼?佛陀用不可思議的智慧神通之力,使聽眾聞解各異,聽聞與了解各各不同,你聽你的,我聽我的,當然聞解各異,當然證果也不同,對不對?有時候一個大根性的人,也許聞了小法,可是他就證了大果;小根性的人聞了大法,可能他證了小果,所以他證果也是不同,所以叫做「不定教」。
所以,我們知道天台宗把佛陀的一代時教,判為五時八教。「五時」,就是華嚴時、阿含時等五時;「八教」,就是「化法四教」加上「化儀四教」──這是天台宗的判法。我們知道華嚴宗把佛陀的一切經教,判為五門──小乘教、始教、終教、頓教、圓教。那麼他們各宗都把自己的宗判為什麼?當然是最特別的、最圓滿的、最頓的,對不對?没有一個人會把自己列為不好的,從這裡我們就知道都是這樣。再來,問題來了
【然既為劣機而設,非勝根所必須,縱曰圓人無不可用為圓法,亦唯俟不獲已時始一援之,而學者又誰肯劣根自居,於是亦皆被棄。】
「然既為劣機而設,非勝根所必須」,這是什麼意思呢?太虛大師為華嚴宗、天台宗的這種設教、判教,深深感慨,說:「然既為劣機而設,非勝根所必須」,兩宗雖然有判教,可是他們的分判是什麼?是勝劣、高低、大小、深淺、圓缺,對不對?圓不圓嘛!所以他們的分判中,有的教法既然是為劣機而設,就不是勝根者所必須了。
「縱曰圓人無不可用為圓法,亦唯俟不獲已時始一援之」。「唯俟」,也只有等到。「不獲已」,不得已,不得已的時候。說即使圓滿利根的人,什麼法都可以作為圓法用,可是也只有等到不得已的時候,才偶爾引用它一下。為什麼會偶爾引用它一下?因為有可能在寫著作時,要引經據典,這一句是出於《阿含經》的那一本,那一句是出於……,所以也只有等到不得已的時候才偶爾引用它一下。
「而學者又誰肯劣根自居」,可是你雖然判教有高低、大小等等,可是學者又有誰肯自認為自己是劣根的呢?又有誰肯把自己安住在是劣根的這個位呢?
「於是亦皆被棄」,因此,中、下法也都被遺棄、抛棄了。因為每一個人一定從高高大法去執取,連中法、下法一定都不願意看一眼了,所以說「於是亦皆被棄」。
【此風至日本而加厲,橫判顯密教,豎判十住心之東密,則除秘密盡排為淺顯,高唱經題之日蓮,則於法華亦捨迹門而僅崇本門。】
「此風至日本而加厲」,你看這種作法,這種情形,到了日本變本加厲更加嚴重了。
「橫判顯密教,竪判十住心之東密,則除秘密盡排為淺顯」,說日本的密教,我們一般都稱它做東密,因為日本在東方,所以都稱它為東密。說這個日本密教,從橫判──同時代的教法來判──把它判成顯教的、密教的,你是學顯教的,我是學密教的。從豎判──修證的次第來判──把它判十住心,當然這是東密的判法,我們就不加以解釋了。橫判顯密教,竪判十住心的日本東密,「則除秘密」,除了秘密教、秘密法之外,「盡排為淺顯」,完全都把其餘的排斥成淺教、顯教。
「高唱經題之日蓮」,「日蓮」就是日蓮宗,日蓮宗跟中國的智者大師一樣,獨鍾法華;可是我們看中國的智者大師獨鍾法華,是從法華做他的主修,他像宗大師那樣的旁徵博引,而且都是實修的;所以天台宗在中國佛教真的是有修有證的一個宗派。而日蓮宗呢?日蓮宗的創始者,人家都稱他為日蓮上人,日蓮就是他的法號;這一位日蓮和尚,他雖是獨鍾法華,可是他怎麼樣獨鍾法華呢?
「則於法華亦捨跡門而僅崇本門」,你看《法華經》總共有二十八品,前面十四品被稱為「跡門」,「跡」是什麼意思?有行跡可循。前面十四品所講的,就是佛陀的一代時教:最初的出家修行、他怎麼的修,怎麼的教導弟子,就在前十四品裡有行迹可循──也就是說前十四品所講的道理,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出家、修行、弘法、入湼槃這個範圍。後面十四品──從十五品到二十八品──叫做「本門」。「本門」是什麼?就是闡述佛陀自身的本地風光,是在無量劫以前,他就已經成佛了。所以這個「本」,是開始闡述他本來是怎麼樣的情形。《法華經》敘述了兩門:「跡門」與「本門」。在「本門」的範圍就告訴眾生,告訴弟子,其實佛陀無量劫以來,他本來就是成佛了;以及成佛的境界是什麼什麼什麼。日蓮宗也是從《法華經》修,可是他卻從《法華經》當中,「亦捨跡門而僅崇本門」,聽說只是拜「大乘妙法蓮華經」這七個字,除這七個字之外,他們是不拜其他的。所以太虛大師才很感慨,說:「高唱經題之日蓮」,什麼經題?法華經的經題──「大乘妙法蓮華經」,或者再加一個「南無」,「南無大乘妙法蓮華經」。那麼高唱經題的日蓮宗,「則於法華亦捨跡門而僅崇本門」。
【今日本雖經明治維新復興,然亦祇有各宗而無整全之佛教。】
「今日本雖經明治維新復興」,明治維新我們知道。
「然亦祇有各宗而無整全之佛教」可是明治維新以後呢?日本也只有各宗,即每一宗都是闡揚自己的宗,卻没有完整全部的佛教。
【中國至清季除參話頭念彌陀外,時一講習者,亦禪之楞嚴淨之彌陀疏鈔,及天台法華與四教儀,或賢首五教儀附相宗八要而已。】
「中國至清季除參話頭、念彌陀外,時一講習者,亦禪之楞嚴,淨之彌陀疏鈔」,這是太虛大師很感慨的話。「中國至清季」,「清季」,就是清末。中國的佛教到了清末,「除了參話頭」,指的就是「禪宗」,你就參吧!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是什麼?就讓你參。「念彌陀」,指的是淨土宗,你就專心的唸「阿彌陀佛」,阿彌陀佛一定會來接引你。「時一講習者」,那麼偶爾舉辦一個講習會講經說法。「亦禪之楞嚴淨之彌陀疏鈔」,他們所講的,也是禪宗的《楞嚴經》,淨土宗的《彌陀疏鈔》。
「及天台法華與四教儀」,剛才我們已經講了,有沒有?及天台宗的法華經、四教儀。
「或賢首五教儀」,或賢首宗的五教。
「附相宗八要而已」,外加相宗八要。
【經律論古疏早多散失,保之大藏者亦徒之供養,或翻閱以種善根耳。】
「經律論古疏早多散失」,經、律、論這些古疏,早多散失。
「保之大藏者亦徒之供養,或翻閱以種善根耳」,把它保藏在大藏經當中的,也只是當成一種供養而已,或者是作為翻閱翻閱,以種善根而已。
【空疏媕陋之既極,唯仗沿習風俗以支持。】
「空疏媕陋之既極」,「媕」,有掩蓋的意思,所以「媕陋」就是掩蓋缺點。「空疏媕陋」已經到了極點,簡單來講,就是空洞粗淺,空洞粗糙到了極點,也就是說沒有把高深廣大的道理闡揚出來。
「唯仗沿習風俗以支持」,這是在什麼時候的事呢?當然就是清末以後,「中國至清季」,對不對?太虛大師便是清末民初的人,他已經感慨到「經律論古疏早多散失,保之大藏者亦徒之供養,或翻閱以種善根耳。空疏媕陋之至極」,你看空疏貧乏已經到了極點,「唯仗沿習風俗以支持」,只是靠著沿習風俗作為寺院的佛教活動來支撐;那麼佛教界的活動都是什麼?這個我們不難理解,對不對?你到處可以看那一個寺廟在辦八關齋戒、打佛七,或者是誦個懺、拜個懺這些;那一個寺廟在舉辦釋迦牟尼佛的慶誕,觀世音菩薩的慶誕,藥師佛的慶誕等等,這樣的佛事來作為支撐。所以說「唯仗沿習風俗以支持」,為什麼說「沿習風俗」呢?因為可能這些佛教活動是從唐朝一直沿習下來的。可是沿習唐朝的法會,真的是盛大的翻譯法會、講經法會,可是到了清末的法會是什麼呢?淨土的就唸唸佛,大家用個餐回去了;非淨土宗的,也許誦一本《金剛經》,也許誦一本《地藏經》或誦一本《水懺》,大家吃吃飯就回去了。用這樣來沿習風俗,就這樣來支撐持續著。
【學校興而一呼迷信,幾潰頹無以復存。】
「學校興而一呼迷信」,太虛大師的那個時代,五四運動,有沒有?興學,打倒孔家店,對不對?禮教是吃人的等等,所以這樣的「一呼迷信」,這個「一呼迷信」,當然就是被一些不信佛的人,登高一呼,這是迷信,怎麼辦呢?佛教「幾潰頹無以復存」!唉呀!佛教的佛像啊、典籍啊,幾乎潰頹而不再存在了,他們燒經典、毀佛像、鄙視出家,佛教幾乎消失了。既然一個時代裡面鄙視出家,那麼誰願意出家?你看早期我們年輕的時候,教育裡面就有那種味道:你只要是講方言,講台語,你就是落伍了,於是大家就一直拚命的學國語,鄙視講台語的;連自己的父母親,自己的阿公阿嬤,都覺得真沒水準──這種風氣是很可怕的!所以「學校興而一呼迷信,幾潰頹無以復存」,佛教三寶,在民初幾乎潰頹而不復存在了。
【迄今欲扶掖以經律論儀,亦尚無以樹立其基礎,】
「迄今欲扶掖以經律論儀,亦尚無以樹立其基礎」,「迄今」,一直到現在。「扶掖以經律論儀」,想要把經、律、論這麼好的教法、戒律扶起來,振興起來,「亦尚無以樹立其基礎」──可是欲振而乏力啊!想要將經、律、論興盛起來,把佛教藉由經、律、論興盛起來,到現在也還沒有辦法可以建立,連最基本的建立基礎,也還沒有辦法建立起來!為什麼沒有辦法建立起來呢?我們不難解,佛法的興盛關鍵在那裡?當然要有法的內涵,其次要有弘法的人。可是年輕人那個時候都被鼓勵去當兵了,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,當時的口號,有沒有?鼓勵青年去從軍。我剛出家的時候,有一些長老有感而發,說:「佛教已經這麼衰弱,怎麼辦呢?」就在那裡研討、研討,研討到最後,有的說:「因為比丘都要過著伴青燈、古佛、吃素的日子,一個人孤零零的在寺廟裡面修行,所以沒有人要出家。」所以,竟然有人家提倡說:「我們中國的比丘,是不是也來學習日本和尚那樣?可以娶妻生子!」拜託!你娶妻生子,怎麼是比丘呢?這些人的頭腦不知跑到那裡去了?你可以作一位在家居士,學佛。為什麼又要是比丘,又要娶妻生子?我就記得那個時候,報章雜誌把它刊得很大篇。接著我們看,太虛大師下面這個文章就很重要了。
【而借觀西藏四五百年來之黃衣士風教,獨能卓然安住,內充外弘,遐被康青蒙滿而不匱,】
「而借觀西藏四五百年來之黃衣士風教」,「借觀」這個「借」,就是嘗試著。這也許是寫文章者自己的謙虛,自己的客氣。他說:「借觀西藏四五百年來的黃衣士風教」,「風教」是什麼?簡單來講,就是它的教化之風,「黃衣士風教」,當然是指宗喀巴大師。「獨能卓然安住」,「安住」,安穩而住。他獨獨能夠高高的特立的安穩而住。「內充外弘」,「內充」,內在是充實的。你看黃衣士教門之內的這些弟子、這些學者,他們內在是非常充實的,所以叫做「內充」;為什麼內在是充實的呢?因為有德、有學、有證,所以內充。「外弘」,而他們對外是廣作弘揚,他們外弘到什麼程度呢?你看「遐被康青蒙滿而不匱」,「不匱」,没有匱乏。沒有匱乏什麼?他們把佛法遠被西康、青海、蒙古、東北九省。「滿」,指的就是東北九省。他們不是只有在西藏弘揚佛法,不是喔!他們甚至遠被到西康、青海、蒙古、滿州。「而不匱乏」,就是說在那些地方佛法都加被到,眾生都能夠無所缺乏的聽聞到佛法,你看它廣被不廣被?太廣被了。
【為之勝緣者雖非一,而此論力闡上士道必經中下士道,俾趣密之士,亦須取一切經律論所詮戒定慧遍為教授,實為最主要原因。】
那麼像這樣的情形,「為之勝緣者雖非一」,造成這麼殊勝的因緣,雖然不是只有一個原因。
「而此論力闡上士道必經中下士道,俾趣密之士,亦須取一切經律論所詮戒定慧遍為教授,實為最主要原因。」「此論」就是指這本《廣論》。造成這種殊勝因緣,雖然不是只有一種原因,而這本《廣論》,「力闡上士道必經中下士道」,所以你不可以跳越,不可以遺漏中、下士道。「俾」,就是使、讓的意思。「俾趣密之士」,讓那些有心想要趣密的人,「亦須取一切經律論所詮戒定慧遍為教授」。「所詮」,就是所詮釋的、所包含的。也就是說你想要趣證高高大法,那麼你也一定要取一切經、律、論所涵攝、所詮釋的這個內涵,這個內涵是什麼?就是戒、定、慧。你一定要從經、律、論當中,去學習戒、定、慧的內涵,一定要取戒、定、慧的精神去修。「遍為教授」,「遍」就是完全。你要完整的、全部的做為你修行的教授;你不能夠遺漏經部,或者遺漏律部,一定是要一切經、律、論所涵蓋的,所包含的戒、定、慧,這樣完整的做為你修行的教授。「實為最主要原因」,這實在就是最主要的原因,也就是說宗大師這一個法教--黃教能夠卓然安住四五百年,一直到現在已經六百多年了--這一本《廣論》實在是最主要的原因。因為這一本《廣論》一直力闡最高高的上士道,一定要經由中、下士道,它這樣不斷不斷的強調,不斷不斷的宣說,當然學者想要登到最高,就一定要每一個階梯、每一個階梯、每一個階梯,都要穩穩的走上去;這就是這一本《廣論》最殊勝的地方,也讓黃衣士的教法,能夠如日中天,一直到現在的最主要原因。
【論云:「如道炬釋:『未修止觀,學習律儀學處以前,是為戒學。奢摩他者,是為定學。毗缽舍那,是為慧學。復次奢摩他前,是方便分福德資糧,依世俗諦廣大道次。發起三種殊勝慧者,是般若分智慧資糧,依勝義諦甚深道次。』若於此次第決定數量決定之智慧方便中僅取一分者,當決定知不成菩提。」】
「論云:如《道炬》釋」,《道炬論》的解釋這麼說:
「未修止觀,學習律儀學處以前,是為戒學」,這裡的「以前」,是包括這個學習律儀學處。說還沒有修止觀,那麼在學習律儀學處以前,是為戒學。
「奢摩他者,是為定學。毗缽舍那,是為慧學。復次奢摩他前,是方便分福德資糧」,「復次奢摩他前」,就包括奢摩他,「是方便分」所攝,所以說「是方便分福德資糧」;也就是屬於福德資糧部份的,也就是方便分。
「依世俗諦廣大道次」,這個是依著世俗諦廣大道次。
那麼「發起三種殊勝慧者,是般若分智慧資糧」,當生起三種殊勝慧的時候,這個三種殊勝慧,也就是在我們科判第十五的地方──智慧的差別有三種:通達勝義慧、通達世俗慧、通達饒益有情慧。所以說生起這三種殊勝慧,是般若分所攝,也就是屬於智慧資糧。
「依勝義諦甚深道次」,這個是依著勝義諦甚深道次。
那麼,「若於此次第決定數量決定之智慧方便中僅取一分者,當決定知不成菩提」,如果對這個次第決定,「次第」,當然就是下士、中士、上士的次第決定,對不對?數量決定,「數量」,就一定要從大乘來講,當然就是要六度,如果再簡略來講,也就要具足了智慧分與方便分,二者不可少。所以說「僅取一分者」,如果二者當中,你僅取一分,「當決定知不成菩提」;是一定知道不能夠成就佛果菩提,也就是不能夠成就佛道了。這一段是太虛大師引《廣論》的一段文來說,所以前面說「論云」,「論」,就是《廣論》。
【福德資糧則人天俱攝,智慧資糧則聲緣相協,律及經論,皆所依止,若僅取一分,不成菩提。】
再來「福德資糧則人天俱攝」,也就是說人天乘都攝持在福德資糧部份。
那麼「智慧資糧則聲緣相協」,這個「相協」,我覺得可以有二種來解釋:
第一種、「智慧資糧則聲緣相協」,智慧資糧,聲緣是相同的;聲聞、緣覺也是要智慧資糧。第二種、為什麼用「聲緣相協」呢?因為要成就佛道,不是只有證聲聞乘的空慧而已,佛道一定是要菩薩乘,一定要行菩薩道。所以說「則聲緣相協」,「協」,就是協助,協助的意思也就是做為大乘的基礎,因此「智慧資糧則聲緣相協」,也可以解釋為智慧資糧是聲聞、緣覺做為大乘的一個基礎;這是智慧資糧的部份。
在這裡我們簡單來講,所謂的福德資糧,是包括了人天乘,人天乘都攝持在福德資糧部份;智慧資糧是聲聞乘緣覺乘,也包括在智慧資糧部份。
「律及經論,皆所依止」,無論你是五乘,你是三乘,你是一乘,總之律及經論,都必須做為依止,也就是都必須依止佛陀所說的經、律、論。
「若僅取一分,不成菩提」,如果僅僅取得一分,也就是福德資糧分,或者是智慧資糧分,那麼你是没有辦法可以成就佛道的。
在這裡,太虛大師都是在說明宗喀巴大師與佛陀的經律論,都判我們成就佛道,一定要福德資糧分、智慧資糧分二者俱足圓滿。
在這個地方,太虛大師又講:
【雖未嘗不別有最勝之歸趣,而確定皆攝入次第之過程。】
「雖未嘗不別有最勝之歸趣」,說宗喀巴大師把整個佛道的道次第判為三士道:下士道、中士道、上士道。判成二分:智慧分與福德分。「雖未嘗不別有最勝之歸趣」,雖然未嘗不是別有最勝之歸趣。為什麼別有最勝之歸趣?譬如說聲聞乘的人,他一定會認為他的最勝之歸趣是什麼,對不對?那麼緣覺乘的人,他也都有他認為最勝之歸趣,但是不管那一乘的人,他們都別有最勝之歸趣。可是確定各乘都攝入佛道的次第之過程。也就是他們都被攝入菩提道的次第中。因此太虛大師下面又說:宗大師他這樣的判法,他怎麼的判法呢?他判佛道有上、中、下三士道;當然我們知道,宗大師這種判法是依著阿底峽尊者的《道炬論》,而太虛大師是在講這本《廣論》,所以他就直接的說宗大師在《廣論》裡面,判上、中、下三士道。雖然三士道有所差別,各有不同的最勝之歸趣,可是對宗大師的這個判法,確定各乘都攝入佛道的次第中,譬如說「五乘共法」被列為下士道,「三乘共法」被列為中士道,「大乘不共法」當然就上士道了;而三士共法,當然連菩薩乘也在內。這只是我簡單的一提,所以說「而確定皆攝入次第之過程」,確定各乘都被攝入佛道次第的過程中。
【於是不沒自宗,不離餘法,而巧能安立一切言教,皆趣修證。】
「於是不沒自宗」,你看,因此宗大師這樣一個判法,他是「不沒自宗」,不失己宗,他己宗的──他的境界、他的內涵──他是不失掉的,沒有掩蓋掉,沒有埋沒掉,他沒有失去己宗。
而且「不離餘法」,也沒有捨離己宗之外的法門,也沒有把其他法們排斥、捨棄。
「而巧能安立一切言教,皆趣修證」,而宗大師非常善巧,適當的能夠安立佛陀的一切言教,都趣修證。也就是宗大師非常善巧的安立佛陀的一切言教,都趣向於修證的法要。所以你只要修佛法,你只要要修證佛道,那麼都跟佛陀的任何一個言教有關係的,也都不能離開佛陀的言教。
【故從天竺相性各判三時,以致華日諸宗之判攝時教,諸宗的判攝時教,皆遜此論獨具之優點。】
「故從天竺相性各判三時」,這個是什麼呢?「天竺」,就是印度。所以從印度「相宗」、「性宗」各判三時;它們各判三時教。相宗判三時教,哪三時教呢?「相宗」,也就是法相宗,法相宗判的人是戒賢論師;所以是印度,不是指中國,不是指西藏。戒賢論師依《解深密經》而判三時教,《解深密經》裡面講到,第一時教就是小乘教,也就是他所講的「四諦相輪」,阿含時那個階段;第二時教就是講「空性」;第三時教叫做「善辨相」,這個善辨相就是講「境空心有」──在唯識宗認為「境空心有」,就是離識之外而無外境,所以叫做唯識;這個在他們認為就是中道的,是中道法。所以唯識宗也就是法相宗,把佛陀的一代時教判為三時。
再來,就是「性宗」。「性宗」在印度,有一位智光論師引《大乘妙智經》證明佛陀的一代時教,也分三個時教。第一個時教,就是為小乘說「心境俱有」;也就是講《阿含經》的時候,對小乘講「心境俱有」。第二時教,就是為大乘的下根說法相大乘的「境空心有」,也就是《解深密經》所講的意思。第三時教,就是對大乘的上根說無相大乘法:「心境俱空」;這就是指《般若經》、《大般若經》,都是「心境俱空」法門。這是智光論師引《大乘妙智經》來判佛陀的一代時教有三個時教。
「法相宗」就是戒賢論師依《解深密經》判佛陀的一代時教分三時。「性宗」簡單來講就是空宗,是智光論師引《大乘妙智經》來證明佛陀的一代時教也分三時。因此太虛大師說:「故從天竺相性各判三時」。
「以致華日諸宗之判攝時教」,這個「華」,就是中國。「日」,就是日本。我們看,「故從天竺相性各判三時,以致華日諸宗之判攝時教」,也就是一直到中國,還有日本「諸宗之判攝時教,皆遜此論獨具之優點」──跟宗大師的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相比,當然它是遜色!所以說「皆遜此論」,「遜」,是遜色。「獨具之優點」,這本《廣論》獨具的優點是什麼?「不沒自宗,不離餘法,而巧能安立一切言教,皆趣修證」,對不對?這是宗大師這本《廣論》的特色。還有第二頁的第五行,「此論力闡上士道必經中下士道,俾趣密之士,亦須取一切經律論所詮戒定慧遍為教授」,有沒有?你看宗大師不沒己宗,他把自己這一宗的主張、觀點顯揚出來,然後也「不離餘法」,一切的佛法,他都不放棄,不捨棄,這就是《廣論》獨具的優點。從印度一直到現在,凡是有判攝時教的大德,他們都沒有辦法可以跟這一本《廣論》相比,跟宗大師的判攝相比。
太虛大師自己一定也是有感而發,對不對?所以他也談談自己了,說
【余昔於佛學概論,明因緣所生法為五乘共法,三法印為三乘共法,一切法實相至無障礙法界為大乘不共法。】
「余昔於佛學概論」,他說:我以前也曾寫了佛學概論。
「明因緣所生法為五乘共法」,「五乘共法」,就是人乘、天乘、聲聞、緣覺、菩薩,就是五乘共法。菩薩乘當然就包括佛了。所以說因緣所生法是五乘共法。
「三法印為三乘共法」,他將這個三法印就是判為三乘共法。「三法印」,我們知道是諸行無常、諸法無我、涅槃寂靜。這個是三乘共法,「三乘」,就是聲聞、緣覺、菩薩,對不對?所以說三法印是三乘共法。
再來,「一切法實相至無障礙法界為大乘不共法」。
【後於大乘本生心地觀經,又增說共不共通法為總要,粗引端緒,語焉不彰。】
「後於大乘本生心地觀經,又增說共不共通法為總要」,這個就是太虛大師後來在《大乘本生心地觀經》,他又增說,共通法與不共通法為整個的要點。
「粗引端緒,語焉不彰」,這是他的一個交待。說我講這個,粗略的引其端緒,也就是我大略的引個開端,「語焉不彰」,但是我語意没有很彰顯明白,没有說得很清楚,也就是他只做一個交待。
【今雖未能獨崇密宗,欣睹三士道總建立之典要,乃特提出以申論之。】
「今雖未能獨崇密宗」,現在我雖然沒有獨崇密宗。太虛大師在中國佛教,被列為是八宗的泰斗,也就是八宗他都有涉獵,所以他說:「今雖未能獨崇密宗。」
「欣睹三士道總建立之典要」,但是我很高興、很欣喜的看到這本三士道總的建立寶典,三士道整個完整地建立的這一本重要寶典。
「乃特提出以申論之」,於是我特別的把它拿出來,作為敍述,讓後學能夠知道。
從太虛大師對宗喀巴大師著作的讚嘆,我們在學《廣論》也會學得特別有信心,對不對?大家可以看,《廣論》是可以用來作實修的論典,讓我們每一個階段、每一個階段都很紮實;去研讀它,然後拿來檢查我們自己的身、語、意,有沒有跟這樣來相應?我曾經聽一位藏傳佛教的大德說:「《廣論》就像小康之家。」小康之家也就是佛道的小康之家,那小康之家是什麼?雖然不是富麗堂皇,可是應該有的都具備了。從初機的--道道地地的凡夫,一直到成佛,《廣論》都已經告訴我們,非常的完整,而且絲毫沒有遺漏。所以西藏這位大德才說:「廣論是小康之家。」也就是必須要有的,《廣論》裡面都有了。
師父開示宗喀巴大師偈讚
我們來講《廣論》太虛大師的讚頌--宗喀巴大師受太虛大師的頂禮讚頌;我們看太虛大師對宗喀巴大師的讚頌,是怎麼樣的心情?怎麼樣的景仰?說
【釋尊大法,策源月邦,派分三幹,化各一方,鍚蘭支那,爰及西藏。】
「月邦」,「月」,指著西方;「邦」,就是國家;「月邦」就是指西方的國家。首先太虛大師這麼講:釋迦牟尼佛的大法,「策源月邦」,「策源」,就是發源;我們就很簡單來解釋它,說:釋尊的大法就發源於西邊的國家。西邊的國家,從中國來講,當然就是指著印度,所以我們常常說:「西天取經。」有没有?往西天去取經,也就是往西方某一個國家--印度大國去求取經典。釋尊大法的發源地就是在中國之西的印度,而大法流傳,「派分三幹」,你看它的支派分成三支,「化各一方」,教化在各各一方。
「派分三幹」,有哪三支呢?「鍚蘭支那,爰及西藏」「鍚蘭」,就是泰國、緬甸等等這些地方。「支那」就是中國。「爰及西藏」,「爰」,發語詞,無義;「及」,與。錫蘭、支那與西藏,就是這三個很主要的支幹。
【蓮華生後,密咒當陽,律像經教,若存若亡,末流猥雜,染風孔張。】
宗喀巴大師是西藏的修行者,所以他緊接著就講到蓮花生大師;西藏的佛教在蓮花生大師之後,「密咒當陽」。「當陽」,就是如日中天那樣的正當興盛。也就是西藏的佛教在蓮花生大師之後,密咒正興盛。可是「密咒當陽」,卻又是怎麼樣的情況呢?
「律像經教,若存若亡」,「律」,就是戒律;「像」,就是佛像、菩薩像;「經教」,就是經、律、論這些教典;「若存若亡」,說它沒有,又好像有;可是說它有,又好像是沒有;所以叫做「若存若亡」。當然我們都知道,有教而沒有人真正的在弘揚;有佛教的三藏經典,卻沒有真正依師的修行的人;當然就會感慨說:「若存若亡。」
「末流猥雜,染風孔張」,西藏的佛教到了末代也是猥雜的。這個「猥雜」,也就是不守清規,不守戒律。於是「染風孔張」,染污之風是張開盛起。沒有守戒律,染污風氣不但生起,而且是非常的興盛。興盛的不是正法,不是修行之風,而是染污之風;它像網的孔是張開的,是非常的興盛。
【大師崛起,濁激清揚,菩提之道,次第宣鬯,下中上士,胥歸金剛,根深枝茂,德隆譽芳。】
我們看「大師崛起」,是太虛大師在讚嘆宗喀巴大師,說宗喀巴大師在這個時候,因緣成熟而興起,出現了。
那麼大師崛起,做什麼呢?當然就是自己修持,自己守戒,而且也把自己所學,自己的經驗弘揚開來,所以能夠達到「濁激清揚」。「濁激」,就是刺激混濁的這一類,刺激猥雜污染的這一輩,當然猥雜污染的這一輩,一定會受到刺激,對不對?畢竟宗大師的戒行、言論等等,跟猥雜染污的這一輩是不同的,所以他們受到了刺激。那麼「清揚」,就是把守戒清淨的他們宣揚起來。也就是讓這些污濁的受到了刺激,讓這一些清淨的宣揚起來。
「菩提之道,次第宣鬯」,這個「鬯」字是古字,同「暢通」的「暢」。「菩提之道,次第宣鬯」,宗喀巴大師著作了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,這本菩提之道的教法,是「次第宣鬯」,宣暢什麼呢?
「下中上士,胥歸金剛」,這個「菩提之道,次第宣鬯」,最後「下中上士,胥歸金剛」,「胥」,就是「都」,都歸之於金剛乘。宗大師把佛陀的教法,非常有次第的分下、中、上,而這下、中、上最後都歸之於金剛乘。於是當下可見的成果是什麼?
「根深枝茂,德隆譽芳」,「根深枝茂」,他紮下了很深的根,枝葉也非常的茂盛。「德隆譽芳」,「隆」,就是又高又深,他的道德是非常的深厚,所以說「德隆」。「譽」就是名聲;「譽芳」,就是他的名聲是非常的芬芳。道德非常的好,名聲非常的芬香,這是太虛大師在讚嘆宗喀巴大師!
宗喀巴大師崛起,因為他守戒清淨,所以濁者受到刺激,清者受到宣揚;「菩提之道,次第宣鬯」,他用菩提道次第的教法,把佛法宣揚出來;最後「下中上士,胥歸金剛」,他的菩提道的最終,要引導下、中、上士,都歸於金剛乘;而他的成果──眼前見到的成果,就「根深枝茂,德隆譽芳」。
接著太虛大師就想到自己的國家,所以說:
【此土禪淨,今亦淪荒,扶戒研理,救之不遑。】
說到中國的禪宗、淨土宗,為什麼太虛大師用禪、淨兩宗呢?因為當時中國最盛行的,就是禪宗、淨土宗。連最盛行的禪宗、淨土宗,「今亦淪荒」。「淪荒」,就是衰微、衰沒。中國的禪宗、中國的淨土宗,現在也非常的衰微,幾乎衰亡。
於是「扶戒研理,救之不遑」,「扶」字,就是拯救。說我們正做著「扶戒研理」的事──「扶戒」,也就是拯救戒律;「研理」,就是研讀教理。「救之不遑」,我們拯救得非常的忙碌,沒有一點閑工夫可以停下來。你看,當時中國的佛教已經非常衰微,非常的衰弱,我們要扶持戒律,研讀經典,要把佛教拯救起來,已經是忙得團團轉,忙得喘不過氣來;這個「遑」的意思,就是閒暇;「不遑」,就是沒有閒暇。我們看一個人非常非常的忙碌,是不是一點閑工夫都沒有,對不對?所以說現在要拯救中國佛教,真的是拯救得幾乎心疲力盡!只要在中國佛教界,一談到太虛大師,每個人都對他非常的景仰,而對他更了解的人,會對他更景仰、感動,當然也會非常的傷痛,為什麼?因為他還沒有看到佛教真正的興隆,就去世了。我們再看後面這一頌,說
【唯師與我,志趣相當,千年萬里,不隔毫芒。】
只有宗大師跟我,「志趣相當」。真的是英雄所見相同,不是英雄疼惜英雄,而是英雄敬愛英雄。所以才說:「唯師與我,志趣相當」,只有宗大師和我的心與志向是一樣的。「千年萬里」,從時間來講,我們時隔了將近千年,其實是六百年,可是在寫文章上,講究用詞的搭配,所以說「千年」,你看從時間來講,我們時隔了千年之久。「萬里」,從距離來講,我們相隔了萬里之遙。中國到西藏,現在是很方便了,你搭機只要幾個小時就到了,對不對?可是在航空還沒開放之前,你要如何去?古代航空還沒有發達,你要如何去呢?像唐玄奘大師,唯一的方法就是騎馬。可是馬總是有一個局限──你翻山越領,有的時候騎馬是很難走的,而馬的體力有可能比人的體力還沒辦法。所以唐玄奘大師有時候騎馬,有時候馬可能病了,可能死了,就沒馬可騎──古時候的交通情況是這樣的。因此他說:「千年萬里,不隔毫芒。」時間是隔了千年,距離是隔了萬里,可是我們心心相通,心是一樣的,「不隔毫芒」,「芒」,就是草的最末端;「毫」,是非常細非常細的毛;「不隔毫芒」的意思,就是我們根本心心相通,連非常微細的毫毛,都没有辦法可以阻隔我們。
【我行未逮,我心正長,瓣香先覺,景仰無量。】
這裡的「行」,我讀了讀,覺得「行」就是指著他的身體,可是還有另外一個意思,指的是他的行誼,他的修為。「未逮」,就是不及,來不及趕得上。「我行未逮」,就是我的身體、我的修為是趕不上你;或者如果單從身體來講,就是我的身體來不及生長在跟你同一個時代,所以我們相隔千年,這是以肉身來講;如果以行誼來講,我的行誼、我的修為是比不上你的,也就是沒辦法與你一樣──這是他的謙虛。可是「我心正長」,這個「長」,就是崇尚的意思;「正」,就是完全、全部的意思。「我心正長」,可是我的心對你是完全的崇尚、效法。所以說我的身體、我的修為,或者是我的行誼,是未及於你,但是我的心對你是完全的崇尚、效法與追隨。
「瓣香先覺,景仰無量」,這個「瓣香先覺,景仰無量」是什麼?古代把很香的那種樹的花,一瓣一瓣的拿來晒乾,晒乾就可以把它薰染,就像我們現在點香這樣,就會散出香氣,所以這「瓣香」的意思,也就是我用這個馨香,來供養先覺,所以說「瓣香先覺」。「先覺」,就是指著宗喀巴大師。我對你「景仰無量」,我對你敬仰是無窮盡的,當然是太虛大師對宗喀巴大師滿懷著敬仰。
真的有心想要修行,而且真的非常的熱愛佛陀的教法的人,讀這一篇文章,會有很深的一種感動,當然無心的人是沒辦法的!我們從這一篇文章裡面,就可以知道太虛大師對佛陀教法的那一種承擔,如果對佛陀教法不了解的人,他有沒有辦法生起承擔的心?所以我們從「此土禪淨,今亦淪荒,扶戒研理,救之不遑」,可以知道太虛大師一直在宣揚佛法,他那想要拯救佛法,振興佛法的一顆心,使他急急忙忙的,馬不停蹄的,所以他也到了海外各國去弘法,更不論是中國了,只要有人聘請,他就去。這是太虛大師對宗喀巴大師他的讚頌,也是太虛大師的志趣。我們一直讀一直讀這偈讚,從當中,我們不只知道宗喀巴大師的了不起,也知道太虛大師的偉大,難怪他在近代被稱為「八宗泰斗」。中國佛教八宗的泰斗,「泰斗」,當然就是領袖,所以太虛大師被稱為中國佛教八宗的泰斗,由此我們就可以知道他的心胸與格局。好!我們來回向。